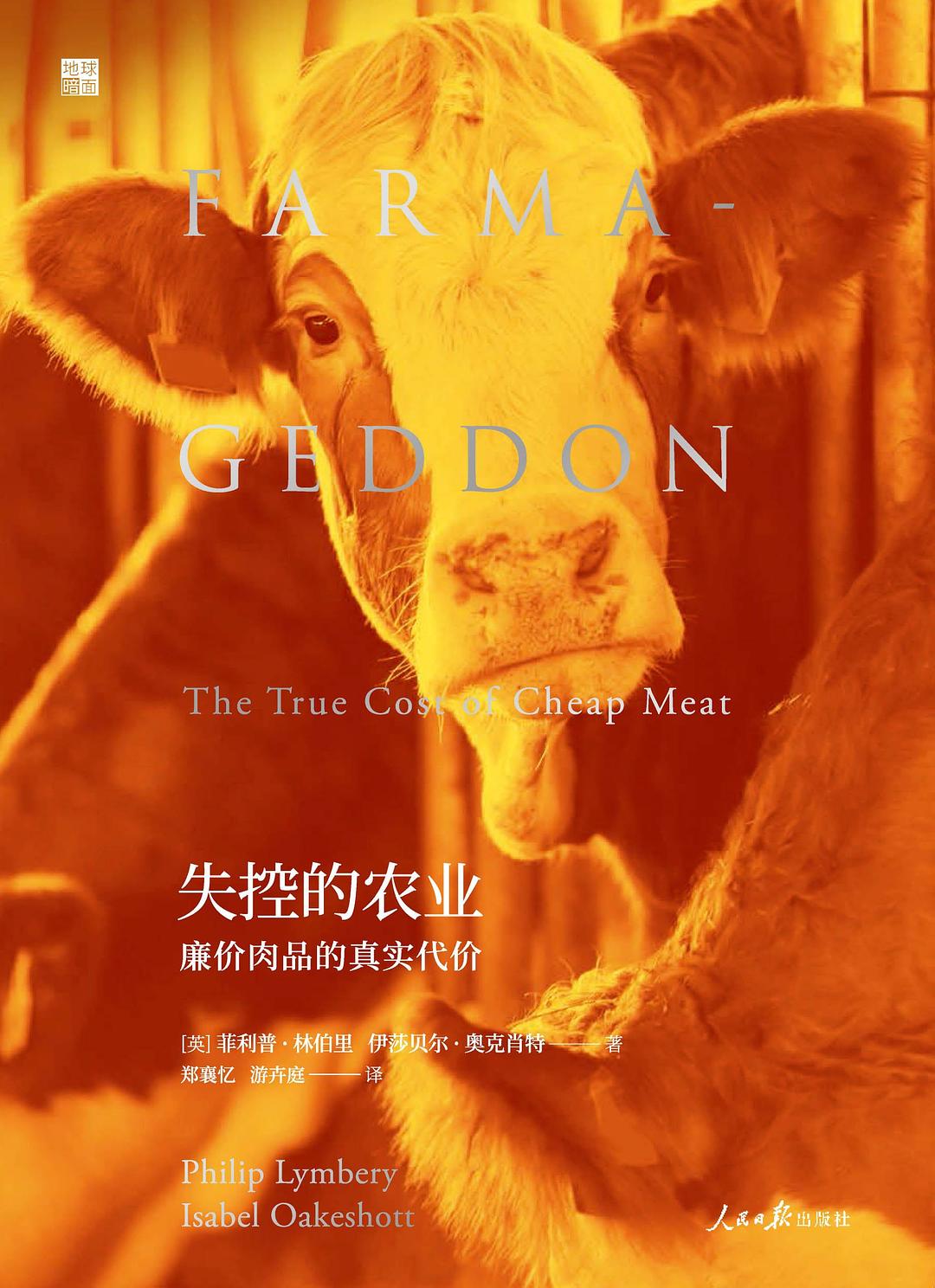二十世纪见证了农业的工业化浪潮,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技术变革也运用在了农业领域,战时的粮食短缺更成为战后各国发展集约化农业的重要动力。1962年,《寂静的春天》的作者卡森就率先发出过食物与农村正面临危机的警告。近日,三辉图书引介了《失控的农业》一书,菲利普·林伯里经历一手调查,再度向我们揭示农业工业化的危机与今天全球食物系统下的隐患。
4月中旬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春意盎然。除鸟儿在枝头高歌,农舍的白色护墙板外,大片黄水仙恣意蔓生。我站在已故现代环境运动之母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儿时房间的窗前,往外凝视着她从小居住到大的阿勒格尼谷(Allegheny Valley)。想象着一名受大自然感召的年轻女孩在果园里采摘苹果,在附近的树林、山丘间漫步,发掘新鲜事物的画面。晨光中依稀可见两根巨大烟囱正将浓浓黑烟喷上蓝天。卡森就是在这个工业与农村比邻而居的世界中长大。然而,在她的有生之年中,两者间的界线逐渐模糊,工业化方法逐渐渗入农业,并造成具有破坏性的恶果。

《寂静的春天》书封
1962年,卡森率先发出食物与农村正面临危机的警告。她的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特别关注在农村施放化学物质的行为,以及这种工业化的农业方式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为了找出“廉价”肉品行销手段背后的事实,以及查明全球食物体系的长触角是如何掌控我们餐盘上的食物,我踏上了一段旅程,现在,我已经在最后一站。我急欲了解,这半个世纪以来,事情是如何发生变化,我们是否有所警惕,以及我们的食物出现了什么问题。在这段旅程中,我走遍了各大洲,从雾霾加州到不夜城上海,从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热带雨林到布列塔尼的海滩。
20世纪60年代,卡森的呼吁跨越大西洋,英国夏普郡(Hampshire)的奶农彼得·罗伯茨(Peter Roberts)也听到了。他是欧洲最先谈论美国的集约化农业(intensive farming)方法入侵的人之一。当他走在自己的田地上,为自家畜养的奶牛挤奶时,罗伯茨因农业上所发生的事变得不安起来。他看着农场动物从土地上消失,进入巨大、无窗的畜舍里;而农牧新闻成为战后农业革命的啦啦队,周围农友不断被这些信息轰炸,被牵着鼻子走上工业化的路线。他认为他必须做点什么。
工厂式农场(factory farm)对动物施予的制度化的虐待行为激怒了罗伯茨,他拜访当时主要的动物慈善机构,要求他们介入其中,但他失望地离开了:因为动物慈善机构拯救的受虐对象侧重于猫、狗或马等动物。罗伯茨虽然沮丧,但不气馁,他与一名律师朋友聊及他的想法。“彼得,至少你很清楚自己的立场,”朋友回应道,“你必须自己采取行动。”
1967年秋天,罗伯茨在自家小屋创立了我现在任职的慈善机构: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Compassion in World Farming, CIWF)。当时,机构只有他一名男子、他的妻子安娜和他们的三个小女儿,对抗的是由政府政策推动,用纳税人的钱补贴,有农业顾问指导,以及受化学物品、制药与设备等公司慷慨支持的产业。面前的阻碍重重。
事实上,问题的种子早在20世纪就已埋下。20世纪40年代,世界几乎处于全面战争状态,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冲突分裂。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全球政治巨大的分水岭,也预告了近代粮食和农业史即将面临重大变革。当炸弹震撼战场时,农村的工业化也已启程。再向前30年,在1910年时,两名德国科学家找到利用空气制造炸药的方法,研究出将大气中的氮气转换成氨的技术,而氨就是制造化学肥料和TNT炸药的关键原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科学家的手中,有机磷神经性毒剂(organophosphate neve agents)的量产技术已臻完美,虽然这种化学武器从未派上用场,但战后,美国公司就将此技术使用在农业上。借用卡森说过的话,在“发展化学武器的时候,人们发现有些实验室制造出来的化学物质能把昆虫杀死……人们用昆虫测试毒杀人类的药物”。原本为生产毁灭性武器而做的准备,成了大规模生产农作物的方法。
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The Creat Depression,亦称经济大恐慌),严重的经济衰退情况持续到战争爆发,从而促使美国国会在1933年通过第一部《农业法案》(Farm Bill),这一系列的农业补贴支持政策至今仍是联邦政府影响粮食生产的主要途径。该法案的推行旨在帮助因市场过于饱和、作物价格低落而处境艰难的美国农民,相关措施包括政府承诺收购过剩谷物,而此举造成了产量毫无节制地快速增加。
在战争期间,许多最富有的国家因来自国外的粮食补给受敌军活动阻断,而经历了粮食短缺的情况,这个惨痛教训让它们体会到自给自足的重要性。因此当战争结束恢复和平后,许多国家开始投注心力在提高国内作物产量上。1947年,英国通过了《农业法案》(Agriculture Act),宣布政府将资助并鼓励以集约化“高效率”的新方式来大规模生产:在一块土地上使用最新的化学物质、药剂和机器设备,以取得最大限度的产出。在美国,制造美国战争机器的军工厂被改造为人造肥料工厂。战时的神经毒气被制成杀虫剂,用来对付新的敌人:农业害虫。植物育种技术使玉米产量暴增,导致玉米价格低廉且大量过剩,最后成为动物廉价饲料的来源。
工业化国家拥有将耕作变成大规模生产程序的方法和动力,但也使得食物和农村遭遇严重且始料未及的后果。以数量取代品质,正是这种情况发生的主要原因。农民被鼓励只需满足商品市场的最低标准,而非尽力生产高品质的作物;抗生素被允许使用在畜禽身上,以抑制饲养了过多动物的狭窄空间暴发疾病的可能性。而注射激素除了可让畜禽快速成长外,还能让畜禽增肥,好尽快供人宰杀。
而在农村,兼营作物种植和牲畜饲养的混合型农场(mixed farming)俨然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单种栽培(monoculture),也就是专门大规模生产单一作物或动物的农场。农作已不再需要顺应自然,同样的作物可以在同块土地上不断反复生长,因为人工化肥提供了一个快速修复枯竭土地的办法,大量喷洒化学物质可以驱逐不受欢迎的杂草、昆虫和其他害虫。农场动物从土地上消失,被赶入工厂般的畜舍;而动物粪肥滋养田地和果园的贫瘠土壤的功能,也被人工化肥取代。这是一种新型农业,将生产线模式应用在饲养动物上,令动物在不见天日的黑暗中动弹不得地度过它们的余生。露丝·哈里森(Ruth Harrison)在其出版于1964年的里程碑式著作中,形容这个时代的人们在他们所饲养的动物身上只看到“人类食物的转换因子(conversion factor)”,她还创造了“工厂式农场”一词。
历届英国政府无视这种农业新体制的隐藏成本,为确保新体制获得广泛的采用,他们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宣导。在争先恐后的生产中,一切都过头了。多家公司开始专门培育能快速成长的动物品种,比如,只需六周就能从小小的复活节雏鸡长成荒唐特大号成鸡的鸡种——比先前鸡种的成长期快上两倍。政府聘雇的一群“专家”顾问要农民加入这个行列,否则他们就会面临破产。我记得彼得·罗伯茨曾经告诉我,有一天农业顾问来敲他家的门。那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们交谈了很长时间,但对方所要传达的讯息很简单:如果你想提高业绩,你必须转为集约化养鸡。也就是建造大型工棚,专门且大量地饲养鸡。他可从大公司购买鸡和饲料,等到小鸡成熟——显然不会花太长时间——再把鸡群卖回给原来的公司,由他们负责宰杀及寻找市场。整个作业干净卫生,工业化且一体化。而罗伯茨所要做的,只是在合约上签字和负责养鸡这种“作物”。
尽管罗伯茨已饲养过几百只鸡,但对于这样的做法他感到不安,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自己作为一个农民在饲养鸡上该有的决定权。这似乎不太对劲。当天晚上,他与妻子安娜讨论这件事。她不假思索地回应:“如果你想这么做,彼得,我不会阻止你。不过,我并不认同这种做法。”许多农友和罗伯茨不同,他们败在了销售策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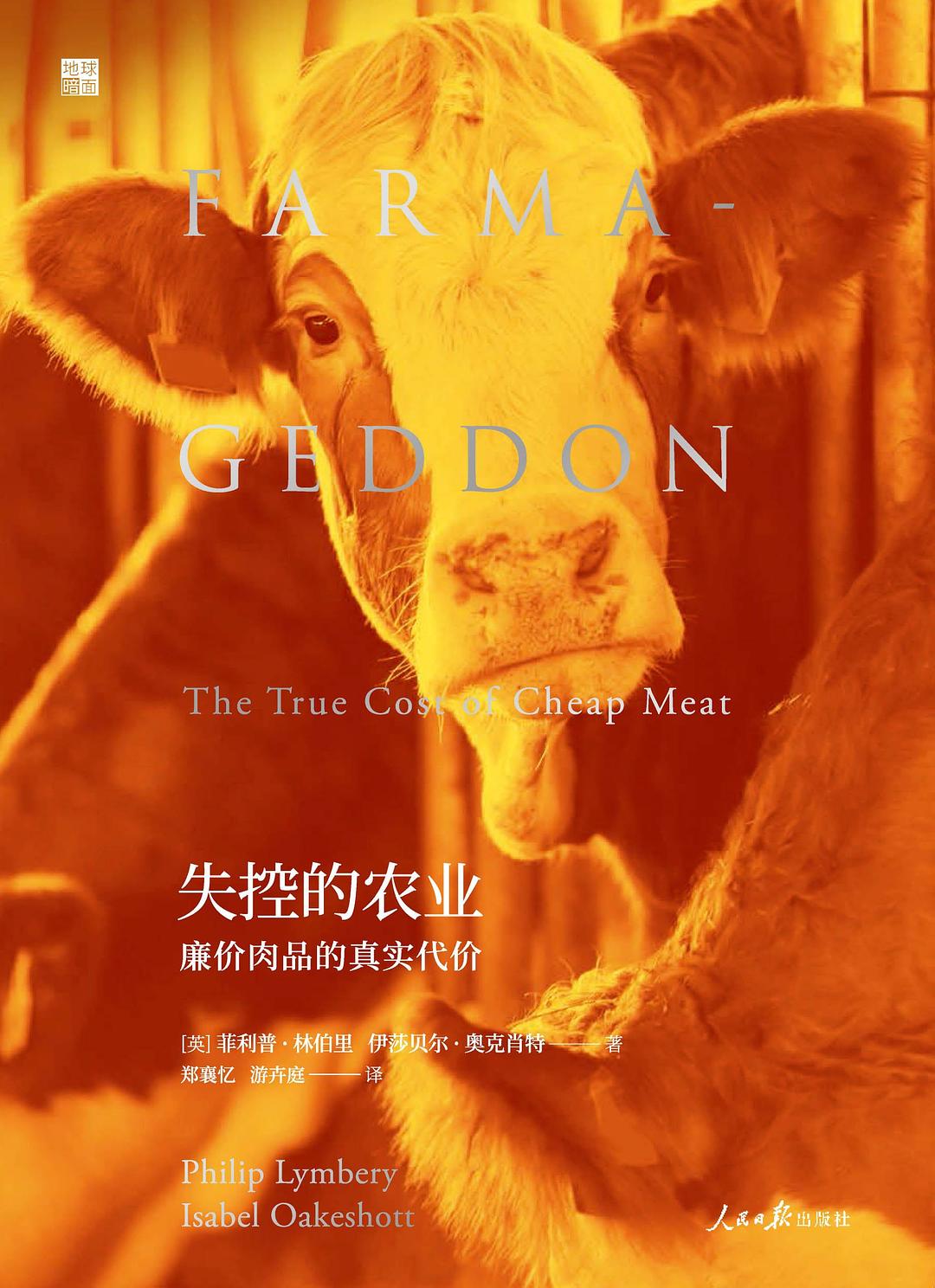
《失控的农业》书封
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农业新方向,至今依旧如此。欧盟在1962年制定备受批评的《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其支出占将近一半的欧盟总预算。欧盟每年补贴近500亿欧元给符合环境相关标准的农民。同样地,《美国农业法案》也拨出300亿美元2作为农民补贴,其中有3/4的费用只用在1/10的农场上——而且通常是最有钱、最大型的农场。而谷类(玉米)一直都是获得补贴最多的作物,因为廉价肉品文化的基础是,用玉米与大豆喂食作为肉品来源的工厂式农场动物,而非用土地上的牧草与粮草。
回头看,不清楚农民究竟是踏上了一条怎样无止境的路:期望投入最小的成本,来创造最大的生产效益,结果却是收益递减。无可避免地,大规模生产势必会压缩农民们的利润空间,遭受这个惨痛教训的农民们体会到,这个诱人的农业新体制并不像人家所说的那么好。他们只好关门歇业。
动物与农作物曾经是互利共生的合作伙伴,但工业化却迫使它们拆伙。大规模种植单一作物的“大麦巨头”崛起,农地随着田篱消失而增大。大自然面对多样性的消失而发出的抗议声已被农药淹没,而昆虫和杂草原本是在大自然法则的控制之下的。土壤被迫日益辛苦地工作。昆虫和杂草被消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减少,寂静的春天更添恐惧——工业化农业的沙漠上再也没有鸟儿歌唱——一如卡森在她那本揭露弊端的书中所记录的。现今全球几乎没有一个角落,不触及某种程度的集约化农业。
近几十年来,情况有所改变,有时甚至变得更好。例如,欧盟已明令禁止将小牛提前放进棺材里——狭窄的小牛栏(veal crates)——让它们在其中终其一生;目前全球也禁用具毒性且破坏力强大的滴滴涕(DDT)农药。
然而,在卡森和罗伯茨发出警告的50年后,食物的生产方式再度站在十字路口上,英国林肯郡的美式大型农场提案就是最佳例证。当时提案要把原本在牧场上放养的8000头牛永久安置在只有混凝土和沙石的畜舍里。英国农村在这场对抗战中翻开了新的一页,当地居民、美食家、名厨、环境和民间社会团体群起抗议。最终,这项提案被撤回。然而关于新一轮农村集约化的隐忧也在同时浮现:更大规模且超集约化(super-intensification)的美式“大型农场”(mega-farming)出现在欧洲的土地上了吗?它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而这种模式的农业对美国本身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很荣幸能在由彼得·罗伯茨所创立的慈善机构、世界领先的农场动物福利组织——“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中担任首席执行官。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目前在欧洲、美国、中国和南非均有办事处和代表处。2011年,我接受董事会主席瓦莱丽·詹姆斯(Valerie James)给予的挑战,揭露原本立意良善、以“为国家与世界供给粮食”为愿景的产业为何会走入歧途:将获取利润看得比供给粮食重要。人类、动物和整个地球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对此,我们可以怎么做?撰写本书的想法因此而生。
我决心探索今日全球食物系统下的真相。我担负起调查记者的角色,追踪可能的线索与举报信息,揭开食物生产集约化的神秘面纱;我也常常利用我的职务,使用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的名片,来让自己脱离尴尬的处境。
两年多来,我与《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政治版编辑伊莎贝尔·奥克肖特(Isabel Oakeshott)及一支摄影组,一起探索左右我们盘中食物的农业、渔业、工业化生产和国际贸易等的错综复杂的网络。我通过自己在各地的人脉,查明应该去哪里,找谁谈话。根据国家与地区在全球化下世界食物体系中的参与程度,我们拟定了一份拜访清单。加州显然是首选,不仅是因为它有诸如好莱坞这样的文化输出,还因为可以在那里看到未来的农作方式;中国的势力逐渐崛起,它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以及饲养猪最多的国家;阿根廷则是全球输出作为动物饲料的大豆最多的国家。我想要亲自看看,这些提供饲料、原料,甚至盘中食物的遥远土地上的人们,如何受到失序的农村工业化的影响。我非常希望从那些参与其中以及受到影响的当事人那里获得第一手资料。这本书所撰述的,不仅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